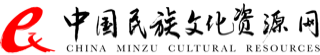体国经野:元明清时期政区变迁与西南边疆经略
“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出自我国古代典籍《周礼》,意思是划分国(都城)、野(郊外、田野)的区域,任命、派遣官吏,管理百姓。其中,“体国经野” 就是今天所说的划分行政区域,这是派遣官吏、管理百姓的基础和前提。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我国历代王朝致力于经略边疆民族地区,逐步形成政治、军事、民族、宗教、边疆开发等诸多领域的政策、措施,其中,设官置守、建立行政机构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在吸收、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西南边疆为中心,梳理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政区演变的脉络,分析边疆治理方略的特点,并提出粗浅的看法。
一、元朝、明朝、清朝西南边疆的政区演变
先秦以来,我国历代王朝都在边疆地区划分政区、设官置守。东周时期,秦国、楚国就在西南边地设置郡、县,此后秦朝、汉朝、隋朝、唐朝、宋朝和三国时期的蜀国、南北朝时期南方各王朝都在西南边疆设置郡(或州、道、路)、县,又因地制宜地设立“特殊政区”。这为元、明、清时期形成省、府、县等政区和多种形式的“特殊政区”奠定了基础。
元代西南边疆政区的设置
在秦朝、汉朝、隋朝、唐朝之后,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在地方政区划分方面,元王朝在先秦以来郡、县政区设置的基础上,进行重大变革,主要是学习金朝派“行尚书省”临时处理地方事务的办法,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下来。元朝的中书省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在全国各地设立“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是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行省下再设置路、府、州、县等政区。在边疆地区,元朝或设立省、路、府、州、县,或设置宣慰司、都元帅府等地方机构,有的地方还派藩王常驻镇守,在西南地区既设有云南、湖广、广西、四川等行省,又有“特殊政区”,派出藩王驻守。其中,广西行中书省于1363年设立,管理今天海南全省、广西大部分地区和广东雷州半岛及其附近的茂名、湛江等地。云南行省辖区包括今天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和越南西北部及老挝、泰国、缅甸的北部地区,下设路、府、州、县,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宣慰司、招讨司、宣抚司和安抚司等土官。元朝还派云南王驻大理、梁王驻中庆(今昆明),云南王与梁王手握重兵,分别镇守在云南西部、东部地区。
在青藏高原上,吐蕃政权于843年瓦解,此后陷于分裂割据状态。在蒙古汗国建立后,西藏地方上层就多次前往联系,1246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与阔端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见,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个行政区。1264年,元朝中央设立总制院(1288年改为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僧徒和藏族居住区的行政事务,在藏族居住区设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管辖区域,既包括今天除昌都以外的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又包括今克什米尔大部分地区、印度的一小部分、尼泊尔的东北部以及锡金、不丹的全部领土;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今天青海的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今天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市及那曲地区的一部分。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设有万户、千户,在基层设置百户、什户。而且,宗相当于内地的县,作为基层政区,在元代西藏地方开始出现。
明代西南边疆政区的变动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地方行政体制上最初继承元朝,仍设“行中书省”,又设都司卫所进行军事控制。1376年,朱元璋将行省的权力实行“三司分治”,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长官互不统属,都直接对中央负责。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掌管一省的行政事务,俗称为“省”,下辖府、直隶州、州、县,在边疆民族地区还设置军民府、御夷府、御夷州等带有“民族自治区域”特点的“特殊政区”。
在西南地区,明朝基本上继承元朝的疆域,既包含今天的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又包括今越南西北部和老挝、泰国、缅甸的北部地区及克什米尔地区、不丹、印度锡金邦。明朝在这一地区的行政机构既包括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广东五个布政司和府、州、直隶州、县,又设都司卫所等军事机构,还设置藩王镇守。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在西藏则采取利用宗教领袖“多封众建”的政策。
在广西,1369年明朝设广西行省,辖境包括今天海南省、广西大部和广东雷州半岛及其附近的茂名、湛江地区,这一年把在元代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基础上所设的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琼州5个府划归广东行省,广西因此没有出海口,580多年间一直是内陆省。至明末,1601年,广西共有11个府、9个直隶州、37个属州和50个县及4个长官司,并在中、东部设置卫、所,管理少数民族聚居的溪、峒及其土官。
在云南,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设立布政司,并设置云南都司,所辖卫所都分布在云南的中部、北部,多在被称为“坝子”的山间盆地驻扎屯田,澜沧司、金齿司、腾冲司3个军民司和其下属的永昌所、金齿所、腾冲所等都曾经是实土卫所,它们既管理卫所的士兵和家属,又统辖当地长官司的少数民族。而且,1382年朱元璋命令西平侯沐英镇守云南,此后沐氏子孙世代驻守云南,1659年清军攻入云南,末代黔国公沐天波随永历帝逃往缅甸。
在西藏,明朝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同时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册封藏传佛教各教派首领为大宝法王、大慈法王、大乘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而宗谿作为基层政权的形式在西藏地区不断得到发展。
明朝建立后继承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又在元代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明朝实施土司的地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广、陕西等7个省,所设置的土司分为文职土司、武职土司两大类,每一类又按级别分为许多种。据龚荫等学者研究,明代的文职土司共有648家,广西309家、云南255家。
清代西南边疆政区的演变
1644年,清军入关,至18世纪中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经过100多年的开拓和经略,清前期形成了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到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到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土。清王朝在全盛时期把全国划分为26个一级行政区,即内地18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对全国实施了有效的管辖。
对于西南边疆,清王朝在1644年清军入关后才开始经营,设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行省,陆续任命总督、巡抚、布政使、提督等官员,建立起军政机构。“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朝中央政府为巩固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明确了四川、西藏、云南、青海的辖区界线,并对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的军政机构进行了调整。就西藏地区而言,清初仍分为四部,即卫、藏、康(喀木)、阿里,雍正五年(1727年)前后,清朝廷划定川、滇、藏的界线,把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地划归云南,把宁静山以东的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以西的地方划为西藏辖地。雍正十年(1732年),清朝廷勘定了西藏、青海、四川辖区的界线,霍尔七十九族中靠近西藏的三十九族隶属西藏,靠近青海的四十族归属青海办事大臣管理。此后,西藏地方就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管理:一为噶厦辖地,即为达赖喇嘛直辖之地;二为班禅额尔德尼辖地;三为驻藏大臣直辖之地,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朝廷命令驻藏大臣直接管辖达木蒙古八旗、三十九族。四是诸呼图克图、法王辖地,即昌都呼图克图辖地、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地、乍丫呼图克图辖地、济隆呼图克图辖地、止贡呼图克图辖地、萨迦法王辖地、波密土王辖地、拉加里土王辖地。在噶厦、班禅辖地,宗相当于内地的县,谿、卡则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
在云南、贵州、广西地区,云贵总督1683年移驻云南。1725年,清朝廷命鄂尔泰以云南巡抚之职管理云贵总督事务,旋升其为云贵总督,1728年任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即为“云贵广西总督”。1734年,清朝廷谕令因“苗疆事务”结束,撤销云贵广西总督,仍称“云贵总督”,结束广西暂时隶属云贵总督管辖的状态,广西仍隶属两广总督管辖。1736年,因贵州巡抚张广泗办理“苗疆事务”有一定成效,为加强他的权威,清朝廷任命他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云贵总督改为云南总督。1747年,贵州“苗疆事务”办妥,且贵州总督调任,贵州总督和云南总督再次合并,仍然称为“云贵总督”。这里所说的“苗疆事务”,就是在今天贵州等地的“改土归流”,也就是在土司地区改设中央派遣的“流官”。从1726年起,清朝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五省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有的土司被革职,有的被降职,有的被迁到别处安置,有的担任了流官。这次“改土归流”涉及的地域广、民族多。根据李世愉等学者考证,雍正时期这五省“改土归流”共革除土司220家,新设流官共152处。
19世纪中期以后,西南边疆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处在“内忧外患”之中。随着西南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朝野上下更为关注西南边疆的治理,不少人主张加强行政管理,又把增设行省、实行与内地一体化和推行新政作为固边守土的重要措施。在云南,由于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驻云南府(今昆明市),总督、巡抚是否能统一事权,成为清朝廷关心的问题。1898年七月,清朝廷裁撤云南巡抚,由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务,九月复设云南巡抚。到1904年,清朝廷考虑到总督、巡抚同城,事权不一,最终下令裁撤巡抚一职,由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务。
对于西藏和川、滇、藏交界的土司地区,中国朝野上下颇为关注,西藏能否设立行省成为争论的焦点。1907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朝廷,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筹边方案,包括开办垦务、改革官制、设立行省、划分辖区、加强边防、兴办学校等。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在北疆蒙古地区设立热河、开平、绥远三省,在西南边疆新设川西、西藏两个省,川西省包括今西藏昌都市和东到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南至乍丫(今西藏察雅)、西至宁静(今西藏芒康)的地区;今天拉萨、日喀则、阿里及附近地区属于西藏省。清政府把这一奏折下发给内、外大臣,让他们发表意见。
清朝廷在1908年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仍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同时任命他的哥哥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希望赵尔丰能统筹安排川滇边区和西藏事务,与赵尔巽、联豫协调好关系,以强硬手段扭转西南边疆的危急形势。但是,由于赵尔丰在川滇边区严厉镇压土司,以强硬手段推行“改土归流”,西藏僧俗上层人士极感恐慌,极力反对他入藏。清朝廷在1909年初不得不解除他的驻藏大臣职务,让他仍然担任川滇边务大臣,联豫仍担任驻藏办事大臣。1909年前后,中央政府在川边、西藏采取“差异化”政策,即在川滇边区推行“改土归流”,为设立行省做准备;在西藏采取渐进的策略,表面上不设行省,事实上又大力推行新政,以之作为治理办法。
赵尔丰是在西南边疆新设行省、实现与内地一体化的积极支持者和实践者。1906年,他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此后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在北至瞻对(属今四川省新龙县)、南至中甸(今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之间的广大地区设立流官。至1911年春,川边地区已经设立巴安府、康定府、登科府3个府和德化州、盐井县、河口县、三坝厅等10多个州、县、厅,并向得荣、江卡等10多个地方派出委员。至此,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区已包括了今天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的昌都市、林芝市的一部分。
1911年5月,赵尔丰奉命调任“署四川总督”,傅嵩炑代理川滇边务大臣,“改土归流”继续进行。8月10日,傅嵩炑向清朝廷上奏《请建西康行省折》,正式请求设立西康省。奏折实际上反映了赵尔丰等人的共同主张,他们认为边疆民族地区以前实行的羁縻政策、土司制度形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不能真正有效地管理这些地方,只有设置省、州、府、县,用“流官”取代土司、土官,才能实现加强统治、巩固边疆的目的。但是,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911年9月4日收到该奏折,此后“文报不通”,而清政府和赵尔丰都忙于镇压革命运动,即使赵尔丰派人“专差送京”,清朝中央政府也难以顾及设置西康省一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土崩瓦解,西康建省一事暂时搁置下来。
二、西南边疆政区变迁及治边方略的启示
回顾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的政区变迁历程,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思考。
第一、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的历史疆域。
中国历史上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疆域。
在秦朝之前,中国文献中就有“五方之民”的记载,也就是东方的“夷”、南方的“蛮”、西方的“戎”、北方的“狄”和中部的“华夏”。在“五方之民”交融的基础上,秦、汉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2000多年间形成“各民族交融、少数民族获得发展→国家统一→各民族再交融、少数民族兴起→国家更大范围的统一”的特点:自220年汉朝灭亡后,经历了近400年的民族交融、少数民族崛起,进入隋、唐的统一多民族大帝国时期,疆域超过了秦汉时期;自907年辽建立后,经历了近300年民族交融、各政权并立时代,过去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先后获得了大发展,并建立了各自的地方性政权,包括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西南地区的大理、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政权等,最终由元朝实现了民族交融基础上的大统一,疆土比汉、唐时期更为辽阔。到了1644年,满族建立的清朝再次实现统一,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历史版图。无论是华夏族,还是边疆地区的夷、狄及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祖先,正是他们之间的交融形成了今天中国境内的众多民族;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汉、唐、宋、明等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王朝、政权,都为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过贡献。
西南边疆地区同样是在各民族共同努力下形成、发展的,这在元明清时期尤为突出。
其一,吐蕃、南诏和大理时期对外拓展疆土,为元朝统一奠定比汉、唐时代更为稳固、辽阔的国土基础。唐宋时期,吐蕃、南诏(后为大理)与中原王朝有过和亲盟会、和睦相处,也有过冲突、角逐。但总体上看,内地与西南边疆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而且积极向南部、西部拓展疆土,使当时的西南边疆得到了稳步拓展。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被划分为以军事组织为主的五大行政区域,即卫茹(中翼)、约茹(左翼)、叶茹(右翼)、如拉和苏毗茹,并设立61个千户,各设千户长,另外有未受册封的小千户长、大五百户长等百户长。这种行政建置基本保留到九世纪中期。南诏、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和大理政权前后延续了600多年,政区和地方行政机构类似于唐朝,不仅设置府、州、郡、县,而且设有“赕”、节度、都督府等机构。南诏极盛时的疆域包括今天我国云南全省,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和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的一部分地区,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的滇国、夜郎和爨氏政权的管辖范围。南诏政权在辖区内设置了赕、府、州、郡、县和节度、都督等军政机构,成功地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管辖。大理政权基本上承袭了南诏的疆土,也根据不同情况设置相应的军政机构,继续进行有效管理。元、明、清三个王朝正是在吐蕃、大理辖区的基础上设置行省等军政机构,经营西南边疆,延续和发展着中国西南地区的疆土。
其二,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的各族人民努力建设家园,地方政权积极经营边地。比如阿里在7世纪就由古象雄统治,后为吐蕃王朝管辖,吐蕃瓦解后其王室的一支西迁,在拉达克、古格、普兰分别建立政权,称为“阿里三围”,元、明时期均属西藏地方管辖。根据黄博对清代西藏阿里基层政权的研究,清朝初年,拉达克强大起来,占领古格、普兰,17世纪中叶西藏地方以蒙藏联盟为基础的甘丹颇章政权派军打败拉达克,设置了扎不让、达巴(今均属札达县)和日土、普兰4个宗和左左、那木如、曲木底、萨让如、帮巴、朵盖齐等6个本,这对于巩固西藏西部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划分政区、设官分职,需要完善的“政策体系”来支撑。
边疆治理是“系统工程”,划分政区、设官置守、建立行政机构只是中国古代治边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与政治、军事、民族、宗教、边疆开发等领域的政策、措施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政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边疆稳固,加快边疆发展。刘君德等学者认为,影响行政区划的主要因素有国体、政体等政治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联系等经济因素,民族分布、民族关系等民族因素,地形、气候、水文、矿产资源等地理因素,行政管理的层级、幅度、手段等行政组织、管理因素,以及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变迁等历史社会因素。这不仅表明政区设置、调整的复杂性,而且说明政区设置只是治边方略的内容之一,需要其他政策、措施的“配套”,才能形成治边的合力。元、明、清各王朝在划分政区的同时,还扶植拥护中央的政教上层人士,驻军防守,清查户口,确立赋税,设立驿站,开展西藏与内地的茶马贸易,逐步形成西藏治理的“政策体系”。
清朝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也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启示:清前期总体上看成效显著,这是因为“改土归流”过程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土司地区改设流官之后,清朝又注重善后措施,既驻军屯戍、修建城池,加强政治统治,又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因此较好地巩固了“改土归流”成果,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清末在川边的“改土归流”,规模、声势都很浩大,但此时革命运动兴起,清朝中央政府权威下降,也无力给予足够支持。1911年,赵尔丰还被调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但不久就被革命军处死,这场“改土归流”以人亡政息告终。民国初年,不少“改流”地区又恢复了土司的权势,新设的政区难以维继。
第三、经略边疆,“政令统一”与“因地、因势制宜”缺一不可。
从秦汉时期至20世纪中期,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边疆不同区域的治理既有统一的政令,又有因俗、因地、因时、因势制宜的措施。元、明、清时期,行省的区划逐步调整,明代基本上确立了今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省级政区地位,但是西南边疆地区政区设置仍然相互关联,主要体现为四个区域性的变动。
其一,清代在设置总督、巡抚时,通常是广西、广东设两广总督,云南、贵州设云贵总督,四川设四川总督。但是雍正年间为了推行“改土归流”,雍正帝就几次调整西南的总督辖区,鄂尔泰在雍正三年(1725年)出任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不久升任云贵总督,雍正六年(1728年)又担任了云贵、广西总督,直至四年后离任回京。
其二,今天四川、云南、西藏三个省级政区的辖区界限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基本确定,20世纪上半期又在它们之间逐步形成了川边、西康这两个新的省级政区。今天西藏辖内的昌都、林芝地区则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西藏、西康地方的反复争夺,到1956年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才明确地划归西藏。
其三,今天广西东南部的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等地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隶属广东省,大部分是在1951年划归广西的,灵山县、合浦县等几个县在1955年、1965年又经反复调整,最后才确定划入广西。
其四,清朝中央政府几次派军进藏,无论是康熙时期两次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部,雍正时期平定阿尔布巴、隆布鼐叛乱,还是乾隆时期派军驱逐侵藏的廓尔喀军队,四川、云南、青海都成为供应粮饷和人员的“大后方”。
第四、边疆治理的政策变迁,既有“时代性”,又体现“继承性”。
边疆地区的政区设置和行政管理体制变动是边疆治理政策及其变化的组成部分,既受到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在20世纪以前的数千年间,“体国经野”、设官置守已成为从先秦到清朝历代王朝管理地方的重要制度,经历了从郡县二级制到州郡县三级制再到省县二级制的演变。周振鹤等学者考察了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指出元、明、清三代,省级政区都是中央管理地方的“高层政区”,县级政区则是基层政区。与此同时,由于不同时期、边疆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中国历代的治边政策经常变化,体现了因俗、因地、因时、因势而治的特点。因俗、因地、因时、因势而治在历代治边中多有体现,不同的王朝都强调过这一点,而且又适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以边疆民族政策为例,秦汉隋唐时期在西南、南部边疆采取羁縻政策,对少数民族首领加以册封,或任命他们管理边疆;元、明时期逐渐发展为土官、土司制度;清前期在沿袭土司制度的同时,又进行了“改土归流”,而且,相关政策一直沿用到近代;清末在川藏滇交界地区再度实行“改土归流”,民国时期也曾在有土司制度残余的地区推行这一政策。
第五、如何看待近代以来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1840年以后,随着列强入侵、边疆危机加深,不少人认为羁縻政策、土司制度形同“封建”,“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并且把行政管理的“一体化”与实施各项新政及“近代化”措施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实行“一体化”“近代化”,才能巩固国防、加快边疆发展。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在边疆地区建立行省、设置县级政区成为朝野上下的普遍共识,于是20世纪初中央政府实施了东北边疆设省、川边“改土归流”的政策,同时,在西藏和内外蒙古设省问题受到各界关注。
1912年至1949年,由于边疆形势依然严峻,这种主张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川边地区在1939年正式建立西康省,刘文辉在西康省成立大会上强调西康建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历史意义,西康“地处极边,自昔视为瓯脱”,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四川徼外之地”或者“吐蕃附属之区,有其地而无其名”,历代王朝“不过加以羁縻,始终未形成一行政单位”,建省以后“封疆明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将渐与内地各行省等量齐观”。二是国防意义,西康“控制三边,毗连藏印,为西陲之门户,滇蜀之屏障,关系国防,至重至巨”,建省之后可以“内促边民之向化,外杜强邻之觊觎”。三是经济意义,西康“地旷人稀,蕴藏极富”,过去开发利用不够,建省之后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当地人民“福利可望增进”,为国家民族也可作出更大贡献。四是政治意义,抗战以来“敌骑纵横,山河残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央为坚定最后必胜之信念,表示长期抗战之决心”,完成西康建省大计,对内可以激励军民斗志,对外“以吾国力雄厚,国情凝固之姿态,昭示世界各国”。从这一讲话可见,西康建省是与抗战爆发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的战略地位相适应的,反映出西康政治、国防地位的提升。同时,这也说明当时有不少人意识到边疆民族地区建省有利于在行政管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即认为边疆民族地区只有废除了土司、土官制度,建立省、县等行政管理机构,才能改变其千百年被“羁縻”的地位,才能“封疆明确”,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才能“渐与内地各行省等量齐观”。
1900年至1949年,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行政管理“一体化”的主张在不仅在西康建省过程中得到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界的认可,而且在云南、广西沿边地区的渐进式“改土归流”中得以实践。这一政策又与清末新政、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建设紧密联系,都是当时中央边疆治理思想、政策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一体化”“近代化”的主张与实践,今天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先秦以来中国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行政区划的变迁及其稳定性、连续性的特点,再考察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和边疆危机,我们就能够较为客观地评论“一体化”“近代化”的主张和实践,既正视某些地区实践中的无视民族地区特点的问题,又充分肯定其有利于抵御外侮、巩固边防、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