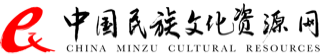“活”在民间的木卡姆

吐鲁番,在戈壁、沙漠和绿洲之中
我的头上,身体上,落满了恢宏的土黄色。吐峪沟的清真寺、麻扎是土黄的,千佛洞、佛塔等遗迹是土黄的,无数古老民居的石阶、葡萄晾房是土黄的,就连火焰山南的树柏沟、二塘沟、斯尔克甫沟,还有鲁克沁绿洲的东南边缘的库木塔格沙漠都像是土黄的册页,漫卷在这火焰般的吐鲁番的绿州内部。
鲁克沁是突厥语,是“居民稠密”的意思。仅鲁克沁绿洲一镇(鲁克沁)三乡(吐峪沟、达浪坎、迪坎尔)就有10余万维吾尔人。在他们创造出的深不见底的绿洲文明中,十二木卡姆无疑是王冠上的饰品。
王冠上的饰品
在新疆北部,最古典、最原汁原味的十二木卡姆在吐鲁番的鲁克沁。
那个冬天的古尔邦节,想听十二木卡姆的期待使我们来到吐鲁番这座古老城市的边缘乡镇——鲁克沁。
冬日阳光下,我看到了这样的乐器:纳格拉鼓、都它尔、龙卡琴、唢呐、弹拨尔。乐器可以体现出一个民族隐秘的文化,它将演绎出持续不间断的人类精神方式。
在我认为,一个地方只会因为把一种潜在的意识化为幻想时而产生舞蹈,只会为了确切地把流传已久的神话颂扬时而产生舞蹈,只会因为让世界看见自己的影子时而产生舞蹈。比如十二木卡姆。
而鲁克沁地处新疆丝绸之路北道,以周围亘古的库木塔格沙漠为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信奉着停滞不动的时间。舞,就这样使这里的居民在世俗生活的状态里与世界达成和谐,颂扬被日月耗尽的每一种劳动的时光,还有被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时光。
十二木卡姆的演出没有固定场所。它的舞台可以是葡萄架下的一块空地、一块地毯;可以是堆积着粮食的打麦场,也可以是在褐色围墙之中。总之,木卡姆可以在不确定的任何地点时间里举行。
在欣赏到十二木卡姆之前,我看到一位白须飘飘的维吾尔族老者双膝跪地,正在抚摩他的纳格拉鼓。纳格拉鼓是用牛皮作鼓面,颜色如褐、状如小水桶,它通常有两个鼓配合。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位抚摸着纳格拉鼓的维吾尔族老人。这是他心爱的乐器,肯定是陪伴了他许多年。时间为这两面鼓敲击出无穷无尽的旋律,鼓面的边缘已经磨损。如果丢弃了这陪伴他多年的纳格拉鼓,他的心就会忘记任何音符,他的手也不可能弹奏出心灵的旋律。他心中的旋律早已在这两只古老的纳格拉鼓上荡漾。
他甚至再也不可能找到这虚幻的复制品。如果丢弃了它们,那么,他对时光的感觉将会失去源泉。
“咚--吧吧,咚吧”
“咚--吧吧,咚吧”
在纳格拉鼓激烈的鼓声中,几位维吾尔族老艺人们走到台前。从演出装束来看,他们毫不修饰,也就是很普通的百姓服装——大棉氅。这么热的天,他又在鞋子外边套了一层毡靴,真是“土”到家了。
在萨它尔的伴奏下,他径自轻声演唱,先是一段散板,缥缈的声音有如天籁。演唱的过程中始终双眼紧闭,这个正在演唱的维吾尔族老人,他一生中所梦见的所有旋律都已在萨它尔弦子的颤动中表现为相逢、约会、别离、祝福;表现为雪山、河流、家园,以及季节的变迁。在这优美的歌词中,找到一切古老的起源。
他紧闭着双眼,似在祈祷,犹入幻境。
然后,达甫(手鼓)进场了。这意味着上板,几位维吾尔族艺人每人都演奏着一件乐器,并且唱了起来。他们的演唱全身心地投入,并不在乎有人是否在听,是否欣赏,沙哑的歌喉挟带着沙石的激流……
维吾尔族老人的弦子拉响,维吾尔族年轻人的弦子拉响,古老的弦子和新的弦子之间相互碰撞,一起流淌。
一曲终罢,当乐声再起时,只见两位维吾尔族长者放下手中的乐器,来到舞者中间,合着纳格拉鼓唢呐激越、悠扬的声音跳了起来,节奏加快,舞姿随之变化多端。
看,他们的肢体在模仿着种种鸟兽的动作,显然是相互竞技。这舞姿来源于劳动者的姿态,来源于动物飞翔或行走时的姿态。你模仿这一种鸟兽,我就专找其克星,你来我往,甚是好看。一切的舞姿就是为把我们的肉体和灵魂脱颖而出,跳到兴致处,那个维吾尔族舞者猛一抬腿,将毡靴猛的甩出——另一位也不示弱,台上台下,有应有和,一片疯狂。
然后,手鼓齐鸣,在许多弦子发出的旋律中,许许多多的维吾尔族舞者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上场了,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
舞者们带着笑容,我在鲁克沁歌舞的世界中看到的都是笑容。笑容是一个有音乐、有激情、有梦想存在的表现。
是的,木卡姆跳到了最后——就是场面欢腾热烈的麦西莱甫。麦西莱甫是以歌带舞,既歌又舞的乐舞形式;是集体舞,所有的麦西莱甫都是一场集体歌舞。男人、女人在围起来的圆圈中,旋转着跳舞。脚踏处,烟尘腾起。无限的欢乐,无限的伤感,无限的幻想。那么多的维吾尔族人,甩着他们古老的、年轻的、彩色的衣袖,一起旋转着跳麦西莱甫。
舞者们旋转的力量瞬间感动了我,撼动了静止不动的每一架时钟。在飞扬的尘土中,他们那些无限的快乐,被我这个异族人看见。
榆树上的老人
在蓝天之下,我们看见鸟飞,看见花开,看见婴儿啼哭,看见一头牛消失在大路的尽头。自然按照它自己的意愿行事。哪有什么意义?但是意义总是会旁逸斜出。
比如那天,我拿出一张照片给人看,有好些人感慨其中的一张,我取了个名,叫《节日》。木卡姆艺人们演出那天,鲁克镇达浪坎乡一下子出奇的热闹,老老少少的,把乡里唯一的一块空地都塞满了。可人还是太多,狭闭的空间,最大密度地集中着人,于是,一些个子小的“巴郎子”,就干脆爬上了路边的树,却没想到,同村里的一个7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汉比他们快了好几步,早早顺着枯草乱藤直挺挺地蹿上来,像一个硕大的果实,把自己“挂”在树上了。尽管是酷寒的冬天,到处是凌冽寒冷的气味,人们说话的时候,连声音都变成一团团白色的气雾。背景也是无限制的白色,雪的颜色。可是这几棵根须暴露的树,因了老人和孩子,仿佛有了生长的快乐,生命体一下子被涨满了,正要吐出新叶,开出花。
孩子在树上,老人在树上,年老的和年幼的尽享其欢。我突然发现,活着,居然还可以这么盎然有趣。
可真正的东西没留在照片上。
看照片的人说:多好的节日景象,可是木卡姆真有这么好看吗?我会不会这么“跑 ”到树上去呢。
艺人们
吐鲁番的木卡姆与喀什、和田、库车的木卡姆相比,多了一层保留远古游牧民族习俗的文化特征。来这里,我想听一听纯的木卡姆演唱,一定是要那种原生态的、纯的人声。
可当地人说,在鲁克沁镇,真正会唱木卡姆的艺人也就那么几个,要找一个原生态的木卡姆艺人不是那么容易了。换句话说,随便走进鲁克沁镇的任何一个乡里,如果不是节日,想要一个木卡姆艺人随便开口就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可我不信,我是真的想听。
他们说,那就去找鲁克沁镇文化站的站长依则孜·尼亚孜。70多岁了,唱了一辈子的木卡姆了。他的家离这儿不远。有多远?三公里多,那个地方就叫三个桥村。
我说,我在报刊上,电视上见过他。在当地,人人都知道他。
在吐鲁番地区,几乎每一座维吾尔族乡村都在葡萄园的深处,泥是最基本的色彩,几乎毗连着维吾尔村庄纹理的精神元素。
村子里都是土路,一间间散发泥腥气息的土坯房,在早春的寂静中显示出自己的符号王国——它们状如碉楼,一色土黄,用土坯打制的墙壁镂出密密的网格状的洞孔。这是当地农民借助吐鲁番火洲的热风吹拂,晾制葡萄干的晾房,又叫“荫房”。
一路上,车掀起土,黄尘滚滚,又包围了车,但还是能看到村民家彩门的图案。都是花,都是鸟,色彩拙朴大胆,如孩童信手所画。我记得2006年从鄯善县城来鲁克沁镇的一路上,也见过维吾尔族人家好多好看的彩门。车子一路开过去,像是走在一条流动的画廊中。我以为鲁克沁的彩门是村民自己画上去的,一问,说是有的是自己家画上去的,但更多的是在吐鲁番一带游走的画匠手工画上去的。
在少数维吾尔族村民的家里,还会看到上辈人留下来的描画着花鸟鱼虫的老式箱柜。这些旧东西如今在农村没人稀罕了,年轻人都讲个潮流,结婚时添制的立柜都是相近的款式,一律是复合板,还镶有一面穿衣镜。这些通通都是外来的,外来的都是昂贵的。可怎么看都是粗陋简朴的,好象现在的年轻人不再需要精致而细腻的东西了。
艾力吾斯曼·哈木提是吐鲁番鲁克沁镇文化站的一位专业的木卡姆艺人,之前,他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
他看起来很年轻,一问,还是一个“70后”。可他并不是从小就会唱十二木卡姆,而是在1997年前才开始拜师傅,跟着一位木卡姆的老艺人学的。
“以前是不懂,师傅唱啥,我也跟着唱啥。后来有一次跟着师傅到外地演出,遇到了一位专家,说我们唱的不是本地的木卡姆,是喀什木卡姆。那一刻,我和师傅一下子懵了。回去以后,又重新花了好几年时间开始学习鲁克沁木卡姆,也就是我们本地的木卡姆。”
艾力吾斯曼·哈木提家里有一块还不到8亩的葡萄地,有了这块地,每年可以有一万八千元左右的收入。除了他的一份工资,家里的10来口人就完全靠这块地养活。
他坦言告诉我:“自从唱了木卡姆,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我家里快70岁的老父亲也像村子里的人一样,养了3只斗鸡,可我没兴趣,看一会儿斗鸡眼睛就困了,就想睡觉了。”
喜欢。
这两个字可以假设是一个生活的借口,它会使你的生活有一个重心,一种秩序。真想追问一声,这一切对他的意义何在,其实不管有没有意义,都得先把自己交出去。
到底是年纪轻啊,几年下来,他学会了用双语(汉语、维吾尔语)唱吐鲁番十二木卡姆。这在当地的木卡姆艺人当中,他算是惟一的。
目前,在鲁克沁木卡姆艺术传承中心的木卡姆艺人就有近30位。2005年前后,鄯善县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成立了木卡姆艺术传承中心,从报纸到广播,从电视到网络,仅2007年到这里来采访吐鲁番木卡姆的国内外媒体就多达3000多人。县上还从财政抽出专项资金,为承担吐鲁番木卡姆传承保护工作的11位主要艺人按月发放了补助。其中有六个人每月发放600元,有四个人每月发400元。其他近20人按社会最低保障发放,每月150元。
85岁的胡加木尼牙孜·克吾尔是个跳舞的木卡姆艺人,在文化站里,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从12岁开始跳舞,到现在已有 73年了。我去过他的家,泥的屋顶,泥的墙,院子里一张破损的大木床上铺着看不清颜色的花毡,院子里惟一值钱的东西,是放在墙脚的一架木轮车。胡加木尼牙孜一直是种葡萄的农民,我想象他在夏季的葡萄藤下辛勤地出入,阳光照亮了他脸上的汗水。如今, 他也领到了每月400元的补助金。这样的待遇,他当然是满意的:“以前讨厌木卡姆的人也有,那时候我们天天晚上唱木卡姆,一分钱也没有,晚上不睡觉,白天到地里干活身上就没劲。地也荒了,要是一直那样子的话,我们不唱木卡姆了。政府给我们补助的时候,我们也高兴得很,越来越(有)兴趣(唱)木卡姆。”

拉艾捷克琴的盲少年
我要去的地方是托万买里乡小学。它离鲁克沁镇很近,车程不过20来分钟。自从新疆维吾尔的十二木卡姆申报“世遗”成功后,木卡姆热也漫延到了这个偏远安静的角落。
托万买里乡小学现在的名称叫木卡姆小学。 因为它是新疆惟一开设有正规木卡姆课程的学校。
从鲁克沁镇往木卡姆小学走的一路上,可以看到好多的古树。一起来的干部说,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呢。从下月初起,每棵古树都有身份证了。不知是否因为正午,村子里相当冷清,有一种懒洋洋的与世无争的闲适意味。
一个身材奇瘦穿着有点邋遢的人蹲在我们路过的一棵古树下。身边的人说,他是三个桥村里的盲人。现在,他靠着树,树是榆树。他的身体面向冬天的阳光,虽然看不到,但一定能感觉到阳光照在他的胸脯上,暖和多了。
几个半大的维吾尔族小孩围着他。他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把艾捷克。
我问:这个人会弹琴吗?
其中一个小孩说:会拉。我让小孩对他耳边说,可不可以让他弹一段。他马上用嘴吹了吹琴身,开始弹了。他弹得不好,断断续续的,曲子不成调,灰绿色的眼睛一直看着脚面,好象那上面是一张琴谱。这么多人围着他,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了。
我没有听完就匆匆上了车,一会儿,又下来了。我在他裸露出来的口袋里放了一张10元钞票。但直到上车我才得知,少年名叫木合买提,今年还不到20岁。他的父亲是这个村子里小有名气的木卡姆艺人。木合买提生下来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也没上过学,但是喜欢热闹,村子哪里有木卡姆聚会,就要人带着他去。他从小就喜欢拉琴,可天赋不高,家里人也就随他去了。我有些懊悔:钱当然有用处,可村子里的人把他喜欢拉琴、喜欢木卡姆看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并没因为这个而施舍他。他应该得到尊重。车走了一会儿,我扒着车窗回头看,那位盲人少年还怀抱着琴,面向阳光站着。
唱木卡姆的娃娃们
与北疆其他乡村小学一样,木卡姆小学几亩地的校园里全是低矮的土房子。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下午,正赶上孩子们刚刚上完木卡姆课。
近50平米的教室里只有6张桌子,这使得近百米的教室看上去空旷而廖落,残旧的板凳倒是摆放了不少。教室里生着炉火,空气里弥漫着炉烟的浓烈气味。可小小的一架铁炉所产生的温度很有限,我待了一会儿,感到身上仍然凉嗖嗖的。
已经有6个年龄很小的女孩子摆好了上课听讲的姿势,全都背着手注视着我们。陆续地,30多个孩子到齐了。他们齐刷刷地站在我的面前,他们的呼吸完全是乡野孩子的呼吸,而且都有一张健康的歌唱着的肺叶。
校长艾克拜尔说,目前这个“木卡姆班”每周上两次课,每节课两个小时,班里一共有33个孩子,都是从几百名孩子里挑选出来的,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6岁。
以“歌、舞、诗歌、乐器”四部分构成的复杂的木卡姆艺术,如何编成正规的课程给刚上小学的孩子们教授?平均年龄只有9岁的孩子们,能否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学会木卡姆2482行的歌词?
专职教授木卡姆的艾力乌斯曼·哈木提,是鲁克沁十二木卡姆的第八代传人,我事先采访过他。他告诉我,木卡姆课程是先从朗诵开始的。他说:虽然孩子们很小,但需要灌耳音。他一般会提一段歌词写在黑板上,要求孩子们先抄下来,然后大家齐声朗读,通常一段6句词的诗歌,他们要朗读10遍以上。之后,才可以唱。
木卡姆中有很多是表现爱情的单曲,是维吾尔族人用琴弦勾勒出众人灵魂境遇的旋律,是有关他们自己的房屋、居住、吃喝和做梦的旋律,是一餐一食、男和女、醒和睡、哭泣和欢情的旋律。这些对于正在度过懵懂期的娃娃们意味着什么,他们能理解吗?
我表达出我的疑问。
艾力乌斯曼笑了:肯定不能。但这个年龄段的娃娃却是学习木卡姆的黄金年龄,他们必须在这个年龄段去掌握极其复杂的木卡姆套曲起承转合的运腔。过了这个年龄,再去学习这些就会很吃力了。
这首单曲“潘吉尕木”是一首与爱情有关的木卡姆。艾力乌斯曼说,娃娃们为了学习这个单曲,已花费了20多天的时间。
现在,领唱的“小巴郎子”一声“噢依——”起序,童音清脆,其他孩子们的小脸一下子全部扬起,全身竭力向上,向着某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圆润、复杂的滑饰音就这样被他们轻描淡写地唱出来,令我吃惊:
这一节具有表演性质的授课,让娃娃们个个兴高采烈,脸上都是笑。他们那么小,还无法理解这首忧伤的爱情单曲的含义,理解这首情歌——如此巨大的内心焦灼,像一面浓烈而苦涩的海,在耳边窃窃私语,又像“光穿透着暴雨,奔驰和炎热”。现在,他们一个劲地把小身板挺直,把声音吊得高高的,好像他们和人间,和这个词没什么关系,他们只想在众人经过的时候放出声音。而最终,远离了想像中的痛苦,获得了像赞美诗一样的纯洁的音色。
突然,一位小男孩打起了手鼓,“咚—咚啪啪”,伴随乐声,教室里孩子们的合唱声突然高了起来。此时,艾力乌斯曼开始了领唱,中年深厚的嗓音音域宽广,深沉有力,和众多轻细的童声融合在了一起,产生了一种很独特,很感人的节奏。
我的眼睛都有些湿了。
艾力乌斯曼说:现在班里只有五个女孩和两个男孩唱得非常好,几乎可以把木卡姆245首单曲、2482行歌词全部记下来。但这33个孩子中,也只有这七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水平。而如果让他们全部唱会,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仅仅10个月是远远不够的。而这7个孩子,都是木卡姆老艺人们的后人,他们在家里就学到了不少东西,进入这个班之前,就已掌握了不少木卡姆的演唱技巧。
鲁克沁十二木卡姆是新疆十二木卡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因其留存得最为完整、历史也最久远。在鲁克沁演出木卡姆的知名艺人中,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在18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上,较为优秀的木卡姆表演者几乎没有,如果再不系统化地去教授,那么这个神奇的艺术门类就要一步一步地走向绝灭了。因此,他们必须在鲁克沁木卡姆的故乡办这样一个学校。
虽然有了正规的木卡姆教程,艾力乌斯曼仍然感到担忧:我们怕小娃娃们出了校门再把木卡姆还给老师。
艾力乌斯曼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学,也只有六年的学习时间,对于如此复杂的木卡姆表演艺术,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而木卡姆表演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无法完全掌握的。
10多年前,这个小学曾开设过一个木卡姆试点班,招收的全都是六年级的孩子,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有几个孩子已经能够掌握简单的乐器演奏了,但这些孩子只学习了一年就毕业了,之后去了别的学校继续念中学后,再也没有继续学习木卡姆。
遗憾的是,在我们走之前得知,鲁克泌仍然没有一所中学像木卡姆小学那样正规地开设木卡姆课程。